|
网赚项目下载 http://kaorouwanfanzhuang.com
他说过的,3年以后,我就回国。 你等我。 说这话时,还是2016年。 凌根本不相信。他在异国,她在广州。相隔一个太平洋,怎么能作数。 有些话,只能当成风,过了就算了。 但2018年春天,她下班,在写字楼下,见到一个人。40多岁模样,高而瘦,衣品不俗。 他走过来,说,我是陈。 她像被什么东西迎面重击。整个人头晕目眩。 “你怎么会在这里?” “我回来了。” 他站在那里,似笑非笑。没有促狭气,也没有仆仆风尘,仿佛只是一个旧友,来接她一起赴宴。 她怔了足足有5秒。 这样的境地,在她从前34年的时光里,从来没有遇见过。 在她上一段寡淡将就的婚姻里,同样未曾发生过。
他是怎么回来的,为什么回来,她一无所知。 只知道,过去几年里,他只是一个ID,存在于她的联系人列表。 谁能想到,ID背后,有一个真的人。来到眼前的人。 她当即开始后悔,今天为什么没有化妆,头发也油了,衣服并不讲究......一下子滋味复杂,半是惊喜,半是懊丧。 “我怕你等太久,提前回了国。” 她想争辩,我并没有等,又觉得多此一举。不如不说。 在广州某个米其林餐厅,凌订了座,说请他吃饭。然后去地下室取了车。一台白色Taycan。 他坐副驾。 车子驶过珠江边,长风过际,广州塔历历分明,他忽然说:“凌,我不走了。” “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决定?” “不突然,准备了2年。” 她再度无言。 她不是拙口笨舌的人,只是这样亲狎,这样悬念迭起的意外,超出了她的应对能力。
他看着窗外风景。 “这条街变了,这里倒是还和从前一样......广州变了好多......到底还是中国好,热闹繁华,充满了烟火气。” “国外不好么?” “也好。好山好水好无聊。” 抵达以后,他们从停车场,乘电梯上楼。 电梯里有镜子。 映着长身玉立的中年男子,和瘦削倦怠的中年女子。她不露痕迹地低下头。 “有没有人说过你气质出众?” 她装作没听到。 当然有过的。 只是这种赞扬,不知几分是廉价的客套。不能当真。 这些年,她因一心做项目,争市场,像工作机器一样拼命,对打扮几乎不上心。 为省事,同一品牌同一款式能一口气买5套,因不想费心去搭配。 这样敷衍,与“美女”二字当然无缘。
但他觉得不一样。 进了包厢后,他伸手,“正式认识一下,我是陈,43岁,中国人。” 她觉得这样一本正经,实在好笑。也伸出了手。 没想到有名堂。 他一拉,她整个人扑入他怀中。 她受惊般挣扎。 他将双手揽紧她的腰,贴近他。
“可以摘一下眼镜吗?”他俯下来,望着她,耳语般喘息。 她心惊胆颤地摘下来。 “怎么了?” 他看着她,“我想看看你的眼睛。” 又凑近了些,“你的眼瞳是深咖色的,很亮,里面有个我”,呼吸可闻,几乎要亲到脸上。
她拼命挣扎,逃到了包厢里的红木太师椅上。 顶头上是一盏暗金紫荆的灯。光流下来,笼着她的脸。有一种朦胧的、荡气回肠的质地。 像是画中人。 “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。”穷寇莫追,他却追着笑。 她坐在那里,惊魂未定。 手在桌子底下拧成了死结。
这个人,如此莽撞,不按常理出牌,太过冒犯,可也......太难招架。 她当即想到,在情场之中,他应该所向披靡,未曾败过吧。立即就灰了一层心。 服务员上了一碟前菜。 量少得像艺术品。 观赏价值,远大于食用价值。
她倒不意这些。 心思早已不在这上头。珍馐与粗食,都是摆设,没有区别。 他终于坐下来,聊些各自的事。 陈是生意人,很有些产业的,在国外不说风生水起,但也有声有色。 但他告诉她:“年初时,我把生意交给了合伙人,我退出来了。” “为什么?” “因为你不在美国。” 这样的决策,原因当然不止于此。还因为,他觉得可以退休了。 多年浴血奋战,都想找一个节点,做一些改变,让节奏慢一点,休息一下。 这几年里,他陆续把一些生意,转到了东南亚。 转回了中国。 办好股权转让+业务交接之后,他几乎没有犹豫,买了回国的机票。十几个小时后,航班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。 他来见她。 践一场迟到2年的约定。
“跟我去日本吧,最近樱花正开,我想和你一起去。”停了一会儿,又说,“我和你说过的,周游世界的时候,我想身边有一个你。” 她说,不了。公司事多,走不开。 他伸过手来,握紧她摊在桌上的手,不许她逃开。 “到了我们这个年纪,其实不用说太多违心话。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光。为什么不简单一些?凌,我们不年轻了。” 几句话,说得她丢盔弃甲。 时光之于少年人,一步一重景。 之于中年人,一步一重天。 留给他们的时间,确实不多了。 他们都有过错误的婚姻,也在红尘之中折腾过,错过。因为一次业务对接,他们接洽上。 再之后,聊得越来越多。越来越深。 她曾问过他,“陈,你的余生,准备怎么过呢?” 他回:“和你在一起。” 余生二字,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。 抓住了,就是一生。 错过了,就是一瞬。 他在商场厮杀多年,她也十几载,都知道,有些东西,是不需要犹豫的。 拼博 ——就算吧,就算看错了,厉练如她,也有机会愈合伤口,风过了无痕,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。 她说,好,什么时候出发? 明天。
签证当然都有。 次日一大早,她跟着他,登上从广州飞往东京的飞机。落地后,有人来接机。 一个在日华人,陈说是朋友。 “全世界各地都有你的朋友?” 他笑,也没有,只是近些年业务涉及了几个国家,跑的地方有点多,认识了一些人。 当晚,他们在新宿的五星级酒店入住。当然两间房。 他倒不急一些事。 洗漱之后,在酒店三楼的日料店吃饭。
餐厅不大。 装修是日式极简风,以竹木为主,精致无尘。
他替她要了饭、纳豆、烤鳗鱼、天妇罗和味噌汤。 自己要了豚骨拉面。 喝一口,眉眼都弯起来,“嗯,又浓又厚,这味儿正宗。”
又上了两碟火炙寿司。 香郁又清简,不拖泥带水,一是一,二是二,吃得毫无负担。 “吃得惯吗?”他看着她,柔声问。 “我最喜欢的就是日料。”她答。 “我最喜欢的可不是日料。” “你喜欢什么?” “吃日料的你。”她白了一眼,他笑,“这不是情话,是心里话。”
吃惯大鱼大肉、烟熏火燎的人,觉得日料像苛待。 她是真喜欢。 雪碗冰瓯,清汤寡水,大都没有油。 味噌汤无油、纳豆无油、生鱼片无油、寿司无油,哪怕料多味浓的拉面,处理得也看不到微末油腥。 量也少,海藻甚至只有一,但色香味考究,正对她的味,也对她的胃。 羹匙
但这一次,因为没有卡好量,点多了。她吃到后来,实在吃不下了。 也知道剩饭不妥,但确实吞咽得艰涩无比。 他不动声色,将她的碗接过去,扒完碗中饭。饮完最后一口味噌汤。说,走吧。 仿佛只是寻常事。 但在她心里,却是石破天惊。
“想去歌舞伎町看看么?” 她没那兴致。只想歇息。人一年长,对观光式的旅行,真的兴致寥寥。 年轻人,才想看得越多越好。 中年后,只想在某个风景旖旎的地方,与世隔绝,看看云,散散步,泡几盏茶,和至交或挚爱聊聊天。 一切都是可有可无的。 但正因为这种可有可无,才养神。
次日去富士山。 有人开了车,专程送他们过去。 陈说,在富士山脚下的小镇上订了一个院子,有温泉,院内也有樱花。 开门就能看见山头白雪。 门口是河口湖。 “风景是好的,就是有些偏,你习不习惯?” 她笑,习惯。正想避世。 他伸过手来,握住她的。她再度不动声色地抽开去。
经过河口湖时,富士山若隐若现。 樱花怒放。 整个世界像一个梦。 她说:“能停一下车吗?好想看看。” 开车的人叫江,说,这里不能停车。陈说,停一下,让她看看。 停下来,风景奇佳,她沿岸走了几步。
一个日本人远远地嚷:“不能停车,不能停车。” 几个人动作敏捷,立即前仆后继地上车。车子一扑鲁就开走了。 真的是一扑鲁。 她正在湖边拍照,一转头,车没了。当即哭笑不得。
因为走得匆忙,手机没开通国际漫游。她电话都不通。 好在懂英文。 正准备去附近找一个小店,借电话打。才走几步,就看见远远冲来一个人,如百米冲刺,一身大汗,满脸惶急。 是陈。 他狂奔过来,一把抓住她的手。 “我差一点丢了你。” 然后拉着她,往前面停车处走。这一次,她再抽出,他怎么也不肯了。“我要保障你在我身边。” 她又听得心跳失序。 他走得快,又拽得紧,她被拉得踉踉跄跄。 他忽然回头笑,“从前抢媳妇,差不多就是我这样吧。” 她也笑。 或许,这一趟旅程,是她一生中最美的际遇。独一无二,从前没有,以后也不会再发生。 既然可遇不可求。 那么,不要言不由衷,不要进一步退三步,用挣扎的时间去感受,也不算枉费了这无上光景。 上了车,江说,“车还没停稳,他就冲下去了,我没见过他这么失分寸的时候。” 她侧眼看看他。 像重新认识。 一下子,心里已有荡漾的柔情了。
抵达旅馆后,她将行李打开,换上和服,去泡温泉。 满池温热。 空气里弥漫着湿而滞的硫磺味儿。
她泡得心旷神怡。 肤滑如皂。 透过百叶窗看出去,窗外正是4月日本的天空。樱花如云如雪,风低低地吹。 真是人间好时节。
出来吃晚餐。 几个人在富士山脚散步。 樱花一树接一树地开,人行其间,像在梦里穿行,从白色的梦中,移到粉色的梦中。 陈说,你站在花树下,像新娘。
她还没来得及反应,江就笑,“谁的新娘?” “还能是谁?” 江呲牙咧嘴,挤兑他,“唷,霸道总裁啊,好怕怕啊......” 两个返璞归真的中年人,像孩子一样,一路追着边闹边打。 此刻近黄昏。 湖水静谧。 路灯已经亮了,投在水中,像两个世界在接吻。 她想到塞利纳的句子:这和平时期,真像天鹅绒一样。
沿湖徐行。 在拐弯处,看见对面有饭馆,准备过去。 那是四五米宽的小路,没有红绿灯,也没有斑马线。静谧幽长。不远处,两辆车开过来,速度并不快。 她懵懵然往前走,被他一把拉回来,抵在他胸口。动弹不得。 然后乖乖站在路边,让车子先行。
出乎意料,车子没有呼啸而过,在十米外停住了,半晌不动,在等他们先走。 他牵着她跑过马路,回头站定,向司机挥手。 一切都是贴心贴意的。 在那个小小的日式烤肉店,吃神户牛肉,在火上燎烫几回,点到即止,入口即化。 又喝了些清酒。
有些烈,和想象的不同。 她只抿了一点,放下来。喝不完的,又被陈接了过去,一口干完。 晚饭之后,江和一帮人先走了。 留下陈,陪她穿过樱花雪,穿过一个异国的长梦,慢慢逛回去。 他牵着她的手,沉默地走了好一会儿。 湖风吹过,人身上的戾气,都吹散了,吹软了。他忽然说,世界这么好,我们都不要和自己为敌! 也没有特别动人的话。 温暖平淡,和日常言谈并无不同,可不知为什么,她听得就想掉眼泪。
“陈,你真正想要什么?” “要什么?我其实没有改变世界的野心。于我自己,这一辈子都不愁什么。但我们都有责任要背负。责任差不多尽到了,我就想为自己谋一个好归宿。” 她在心里说,我也是。 这些年,她几乎不要命地拼,拼生活,拼事业,拼荣誉,拼成就。 成功当然厚待每一个拼命的人,但幸福却无法在一个充满刀光剑影的人身上驻留。 她离了婚。 也接触过几个男人,都受不了。说她眼高过顶,不是宜家宜室之人。 陈看了看她,“凌,你不是。你非常特别,气质骄傲,但又有抑郁倾向。”
她几乎又要落泪。 “你喜欢抑郁倾向的人?” “不。是因为你这样,所以我喜欢这种气质。” 说起来,如果网上交流也作数,他们算是故友。她对他的了解,仅限于他们的交流。 但他是知道她的。 在国内,他人脉扎实,详细地打听过她的消息。有一回,她在微信里说,有个项目出了些问题,焦头烂额。 次日,有人出现在她公司。 “老陈让我过来帮帮你。” 她那时便知道,他真的会回国。也真的会出现。 有一段时间,她的办公室每日有花送到,玫瑰、百合、芍药、马蹄莲、郁金香...... 她不知是谁,有这样的耐心。 有一回问他,他说,“你只需知道,你配得上所有的美好。”
“陈,你说,拼博的尽头是什么?” 她站在富士山下的长风里,站在温柔的暗夜中,问他。 “是我们。”
次日起床,凌开通了国际漫游。 信号一通,涌进了无数信息。她开了视频会议,处理了些杂务。 好在都是日常事务。处理起来不费神。 两小时后,她站起来,洗了头,洗了澡,换上白色休闲装,沿着花路,在湖边闲走。 满川繁花,半湖金阳,一线流光。 一切都恰到好处。 便觉人生如此,朝斯夕斯,便不算亏待。 陈不知从哪里借了辆单车,跟在她后来,追上来,远远地喊,“喂,那位中国姑娘,我载你啊......”
凌回头,看见他像个孩子,兴高采烈地蹬。 她跳上后座。 扶着他的腰,踢着小腿,穿行在樱花丛中。
到了一处地方,他们停下来,坐着歇了歇。 她躺在花树下。 透过指缝看太阳。阳光透过来,映得手指澄亮如霞光。 他将落花一瓣一瓣地,捡起来,又一瓣一瓣地,在她的胸口,摆成一个心状。 这真是撩人至极的一幕。 整个人又难堪,又难忍。到后来,他每放一瓣,她就暗暗颤栗一下。 凌 “好痒,别放了。” 他依然放。 “我要在你心口,摆上我的一颗心。” 她当即就想到了一些有的没的。
等到结束时,她感觉自己像度了一次劫,或经历了一场别的什么。 他也躺下来。 “凌,你喜欢这里吗?” “喜欢。” “如果喜欢,我们在这里买块地,留下来。好不好?” 她以为他随口一提。 没想到两天以后,有人来旅馆找他,谈地的事情。 他用流利的日语与对方交流,偶尔转回头看她一眼。她坐在另一边,饮着茶,开始猜测他的往昔,他的实力与真心。 这样的男子,真的会属于我吗? 江已经回了东京。 其他人要么去了大阪,要么去了京都。只有他俩,依然留在小镇上。 有天搭了车,去海边,在太平洋的大风里,听见有人用汉语高声大喊: “XX,我爱你,我会陪你周游世界,陪你白头到老……” 一旁的女生满脸泪水。 陈在旁边说:“我心里的声音比这更大。”
回来的时候,他们沿着湖边,往旅馆慢慢走。天空像一片广袤的毛玻璃,那么蓝,那么澄澈,那么让人费尽心思。 长风阵阵,斜阳时隐时现。 她不知怎地,走到了前面。 他跟着她的脚印,一步步地跟。 她往左走。他也往左。 她往右。他也往右。 踩着同一块地砖,拂过同一枝花。 她简直没了办法。 后来,天色就晚了。 再后来,他开始唱歌。 不成调的,随心所欲的,让人忽然就动了心的…… 他说:要不,结婚吧!
那时候,山湖俊美,岁月安详。 她感觉日子就像悬浮于半空的云,慢慢降到了地面。踏实,笃定,可亲可爱,可依可靠。 世界真好。 活着真好。
有天晚上,他们在旅馆喝清酒。 月色如水。 灯火倒映在水中,错落有致,像一串音符。 侍者来了几次,一盅一盅地盛。她说,少喝点儿。 他含糊着接话,“良辰美景,佳人在侧,怎能不喝一点儿?” 一盏接一盏,慢慢就多了。那晚,他们各自回屋。午夜的时候,他趁着醉意,去找她。 凌,我们做爱吧。 她推开他。 “我不是一个好惹的人。” 他走过来,将她抵在墙上。“我这人,就是喜欢挑战。” “我很麻烦。” “我扑摸滚打这么久,就是为了不怕麻烦。”
那一晚,他躺在她身边,和她讲了一个故事。 一位忠臣遭到诬陷,被发配到荒岛上。 历尽艰险,双目失明。 多年后,叛乱平息,皇帝知道自己冤枉了人,派人请回他。 已经目盲的老人,面对这封迟来的诏书,说,即使上面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太阳,我也看不见了。 “凌,我们不要等到看不见。” 那一晚,他恢复成赤子,赤裸相对。以肉身,以往昔。 “我睡过不少人。” “我猜到了。” “我也爱过不少人。” “嗯,你很诚实。” “但只有你,让我想和你一起老去。” 凌不作声。 让她怎么反应呢?她从未想过,她的生命,竟会与他有连接。 一切都在预设之外。 作为生意人,她深知这样的项目风险不可控,时间成本大,回报未知,代价未知。 所以一时之间,不知是该停止项目运营,还是该继续观望。
“认识你以后,我认真地想了一个问题,当身体越来越差,睡眼昏沉,白发苍茫,我该怎么过。 那时候,性成了奢侈。 人生不再需要去向外走,去计算于数据的增加,活在存量里,那时候,我希望有谁陪在身旁。 是你。 凌。 凌。你让我想到了余生。想到日暮途穷时,有你在,就不怕了,就能安心了。” “我一直想问,为什么是我?” “你的人身上,有一种‘定’,目标坚定,始终如一,在自己的路途上稳稳当当地走。这世间已经很少有人做得到的。你难得一见。” 她翻过身,看着他。 看着这个来之不易的男子。 看着他说话的唇。 吻下去。
或许有些情感,来了,就是福份。守住底线,接纳即可。 毕竟,有些爱,一生只此一度。 一度即可一生。 你会在哪里留下来? 你呢? 我们趁着还有力气,四处看看,走走,累了就在当地买个院子,呆在那里。就是不久呆,偶尔去看看也行。 我喜欢广州。 那我们就留在广州。其实一年前,我已让人帮我买了套别墅,已经装修好了,能看见海,清晨的时候一开门,海风就能吹过来...... 我也有。可能没你大,但花开得很好。 离开日本的前一天,江来接他们。大家在居酒屋喝清酒。 包厢简洁。 灯光委婉。 旅居的人聊旅居岁月,移民的人讲移民光景。 她忽然觉得,宁和就是此时此刻。 窗外樱花开满,太平洋的风不分地域地吹,而我们在不同的语言里,将酒杯高高举起,将心事略在后头。 她说,我得先回国,公司有事要处理。 而陈要去澳洲,也要处理一点紧急事务。 或许这样的开端,也就注定了他们以后的相处模式,聚少离多,每一次相逢,都珍贵得一夜千金。 太多时间不凑巧。 但也有太多未知。 太多惊喜。 两周以后,他在新西兰给她电话,来奥克兰好吗?我帮你买好了机票。 她没去。 她周旋于公司杂事之中,无法脱身。 第二天,他回了广州。又是一个下班时,又是一个黄昏。她走下来,看见他。 “走,带你去看我的房子。”
那是个占地近600平的院子,花园里错落有致。家具名贵。四层楼功能分明,设施更是堂皇至极。 她本以为,自己的房子已经够讲究,一比较,显得太过潦草。 在三楼阔大辉煌的主卧,他走过来,拥着她,悄悄耳语,“欢迎回家。” 她环上他的腰,半是央求,半是表忠心,“陈,我不是游戏的人。” “我是认真的。” 他将她带到一楼,在客厅一角,拿出一个手提包。 一拉开,几十份文件、证件、证书,一哗啦地,都摊在她面前。 红红绿绿,错综复杂。 有英文的。 也有中文的。 “这是我所有的证件,能证明我的身份、资产,希望你能感受到我的真诚。” “为什么给我看这些?” “我们都很忙,我还有业务要打点,你有项目要运作,既然你总是担心,我想,不如用合作洽谈的方式,将所有能证明自己的东西抛出来,向你争取一份信任。” 在那个夜晚,海风源远流长地吹过来。 她站在一堆房产证、身份证、绿卡、股权证书之中,拥抱他。 拥抱她的余生。 他的末日。 窗外春意浓浓,生命何其短暂。 既然这一生,总有坎坷要走,有未知要泅渡。不如就在那个人身边,就着往事下酒,摘取岁月煮茶。醉生梦死,尽情欢乐。 痛了,就着风雨哭一场。 开心了,当成意外的获得。 就不存在得失算计的问题。 这样想着的时候,她站在6米挑高的客厅里,笑着,啪嗒一下,摁亮一盏灯。 他走上来,从后面环抱她。 南方的风悠长而透明。 穿过他们的窗。 穿过他们的千里红尘,人间岁月。 他们的余生烟火,已经波澜不惊地开始。荣华沉下来,泡在民间光阴里,化为一半家常,一半人生。 作者:周冲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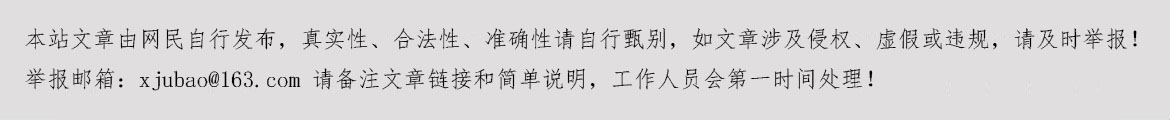
|
 鲜花 |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分享
邀请